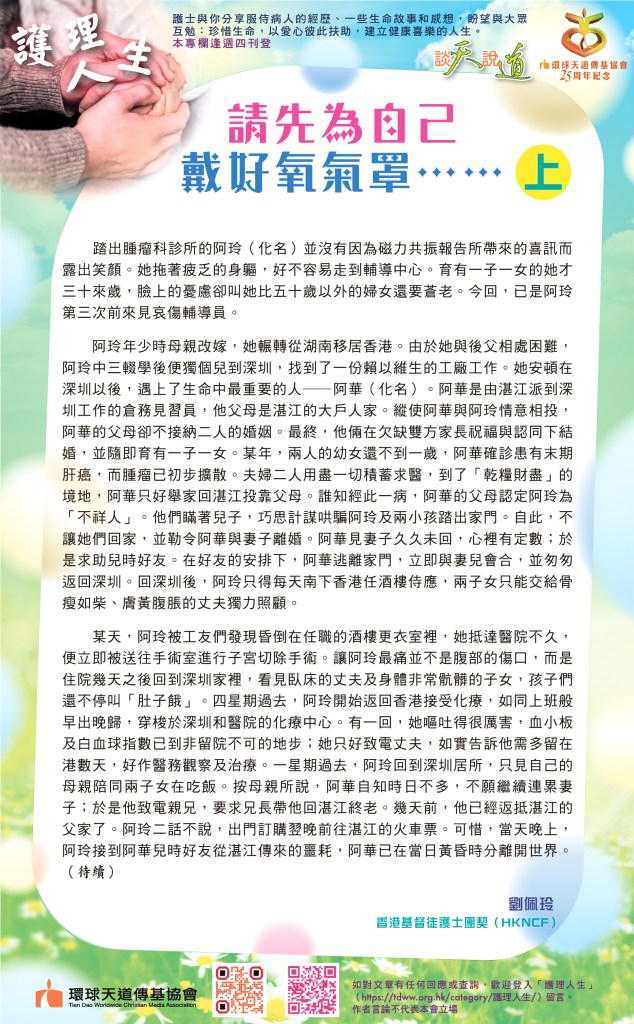踏出腫瘤科診所的阿玲(化名)並沒有因為磁力共振報告所帶來的喜訊而露出笑顏。她拖著疲乏的身軀,好不容易走到輔導中心。育有一子一女的她才三十來歲,臉上的憂慮卻叫她比五十歲以外的婦女還要蒼老。今回,已是阿玲第三次前來見哀傷輔導員。
阿玲年少時母親改嫁,她輾轉從湖南移居香港。由於她與後父相處困難,阿玲中三輟學後便獨個兒到深圳,找到了一份賴以維生的工廠工作。她安頓在深圳以後,遇上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──阿華(化名)。阿華是由湛江派到深圳工作的倉務見習員,他父母是湛江的大戶人家。縱使阿華與阿玲情意相投,阿華的父母卻不接納二人的婚姻。最終,他倆在欠缺雙方家長祝福與認同下結婚,並隨即育有一子一女。某年,兩人的幼女還不到一歲,阿華確診患有末期肝癌,而腫瘤已初步擴散。夫婦二人用盡一切積蓄求醫,到了「乾糧財盡」的境地,阿華只好舉家回湛江投靠父母。誰知經此一病,阿華的父母認定阿玲為「不祥人」。他們瞞著兒子,巧思計謀哄騙阿玲及兩小孩踏出家門。自此,不讓她們回家,並勒令阿華與妻子離婚。阿華見妻子久久未回,心裡有定數;於是求助兒時好友。在好友的安排下,阿華逃離家門,立即與妻兒會合,並匆匆返回深圳。回深圳後,阿玲只得每天南下香港任酒樓侍應,兩子女只能交給骨瘦如柴、膚黃腹脹的丈夫獨力照顧。
某天,阿玲被工友們發現昏倒在任職的酒樓更衣室裡,她抵達醫院不久,便立即被送往手術室進行子宮切除手術。讓阿玲最痛並不是腹部的傷口,而是住院幾天之後回到深圳家裡,看見臥床的丈夫及身體非常骯髒的子女,孩子們還不停叫「肚子餓」。四星期過去,阿玲開始返回香港接受化療,如同上班般早出晚歸,穿梭於深圳和醫院的化療中心。有一回,她嘔吐得很厲害,血小板及白血球指數已到非留院不可的地步;她只好致電丈夫,如實告訴他需多留在港數天,好作醫務觀察及治療。一星期過去,阿玲回到深圳居所,只見自己的母親陪同兩子女在吃飯。按母親所說,阿華自知時日不多,不願繼續連累妻子;於是他致電親兄,要求兄長帶他回湛江終老。幾天前,他已經返抵湛江的父家了。阿玲二話不說,出門訂購翌晚前往湛江的火車票。可惜,當天晚上,阿玲接到阿華兒時好友從湛江傳來的噩耗,阿華已在當日黃昏時分離開世界。(待續)
劉佩玲/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(HKNCF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