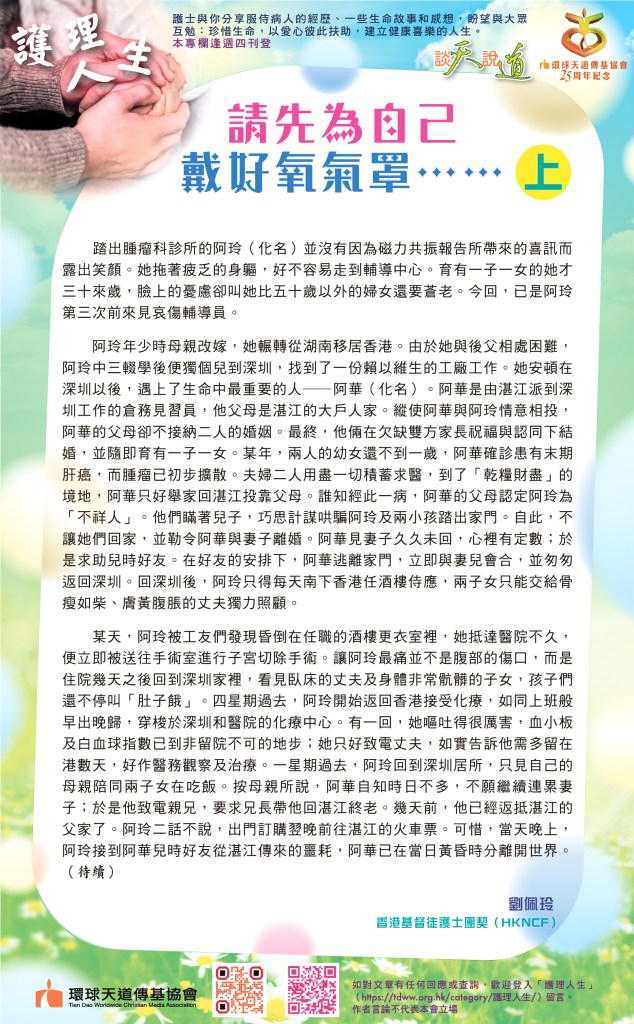阿玲(化名)東歪西倒,終於抵達湛江的夫家,只求見丈夫最後一面;然而,她被拒於門外。翁姑對她惡言相向,怒斥她「自私,貪戀香港的浮華,不理子女及丈夫的死活,不配做阿華(化名)的妻子……」此外,他們告訴她,阿華的遺體已火化,骨灰已被安置妥當。如今,他們既與她恩斷義絕,就互不相干,著阿玲不要再打擾他們。阿玲無奈之下,憤然離開了湛江。
七年過去,十歲的兒子、九歲的女兒和阿玲已定居香港。抹片報告把潛藏在阿玲心底黑洞裡的悲慟再次翻出來。或許,喪夫的哀慟可暫且擱置,但那段存放在腦海的控訴:「自私,貪戀浮華,不理子女及丈夫死活的不祥人。」歷久常新。最可悲莫過於這無稽的責難竟變成阿玲多年來自責、愧疚和鬱結的源頭。連同今天的複述,阿玲已第三次向輔導員表達內心不能原諒自己的愧疚和鬱結。輔導員還是安靜並真摯地傾聽阿玲,待她盡情宣洩情結之後,輔導員才輕柔地向她一一轉述以下生活實況的守則。
「阿玲,記得那次你和兒女去桂林遊玩嗎?當飛機正要升空之際,機艙服務員說了甚麼有關機艙安全及求生的守則呢?」阿玲的眼神仍是一片模糊與悵惘。輔導員歇了一歇,再清晰地說:「他們不是說『若遇上緊急的情況,先為自己戴好氧氣罩,然後才為同行有需要人士(如小童或長者)戴上氧氣罩』嗎?」說罷,只見阿玲揚起眉毛、瞪大眼睛,身體向前傾,緊緊地擁抱著輔導員不放。良久,她才放開雙臂,淚如泉湧地說:「多謝你!多謝你!你為我解開了這個多年的死結。多謝你!」輔導員故作不解,請阿玲講述那是怎樣的結,又是如何被解開?
此時此刻,阿玲的眼眸發出前所未見的光亮。她娓娓道出:「原來我並不是如他們所講的那麼自私。回想起來,若果我當時沒有『戴好自己的氧氣罩』,我並沒有回香港完成我的化療,我怎能活下來照顧我的子女呢?丈夫是末期肝癌,那是死定了。就算我放棄治療我的癌症,就算我留在深圳日夜對著丈夫,他還是要死!如果我並沒有硬著頭皮死命地撐,我哪有治癒的機會?今天,我的子女才不致於失去爸爸後,同時也失去我。就是因為我為自己『先戴上了氧氣罩』,然後也隨即為他們戴上了。對於丈夫,我真是有些虧欠,但我決不是自私、貪戀浮華、置丈夫與子女不顧啊!」
感謝主,阿玲的心結解開了!作為醫護的你和我,在協助病人及其家屬之先,我們是否已經「扣好自己的安全帶、戴好自己的氧氣罩」呢?在生死教育的範疇裡,你解不開,又是怎樣的心結呢?
劉佩玲/香港基督徒護士團契(HKNCF)